叶弥可能就是本雅明所怀念的那个“讲故事的人”,这其实是面对毛茸茸的历史图景和盘根错节的故事纹路,而采用的一种不引导、不归纳、不扭曲的“虚构”态度,借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说法,这态度非常“诚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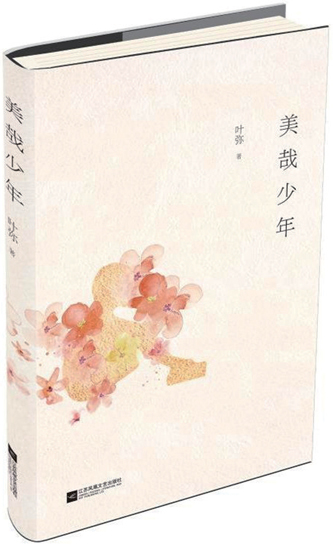
情欲充盈的时刻,革命从天而降,这是叶弥长篇小说《风流图卷》里的一个场景。欢愉滋生得如此自然,如同“满街的白兰花开着”,暴力虽迅疾粗暴,但是也有山雨欲来的提醒。于是,这个暴力和欲望并置的场景便有了多重意味。革命与暴力绞杀了情欲,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看法。在大多数类似的场景中,读者会习惯性地将爱情、身体、欢乐与革命、暴力、禁欲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在同一语境下水火不容。前者的存在是为了批判、控诉后者,进而达到对作为总体的某段历史及其意义的消解和否定。后者亦常常被简化为非人化、非意志化的机械性力量,它要么被别人操控要么操控别人,从而有目的地或者盲目地摧毁、拆解后者。“革命”与“机器”这两个词汇组合成“革命机器”这个常用词,大约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革命绞肉机”无非是更为极端的说法。
很显然,叶弥不愿止步于此。不过这已经显示了叶弥在处理类似主题时的与众不同。叶弥从1958年和1968年这两个敏感的历史节点开始讲述这些故事。前者往往与反右、大跃进等重大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后者则涉及“文革”爆发、武斗席卷全国、军管城市等不同阶段。重大的历史时刻接踵而至,革命的热情和实践亦逐步升级。然而,在集体性创伤冷静铺展的同时,情爱故事却依然摇曳生辉,权力、性、暴力、伦理之间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于是,故事里弥漫着奇妙而暧昧的氛围:革命机器发出的巨大轰鸣声中不时传出情欲的低沉呐喊声。与其说这里传达出的是关于反抗的意义和隐喻,倒不如说,革命更像是催化剂,反倒激发出欲望、伦理,表现出更丰富的层次和意义形态。
叶弥试图描述的故事和观念大约是:或许历史的表情本就没那么僵化,情欲和革命本都是构成历史的“自然”因素,皆在大历史的纹理、肌质中生长、蔓延。为了争夺历史的阳光和水分而相互抵抗、消解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面相。刻意去寻找扭曲或毁灭故事的眼睛,大约会忽略历史的其他表情。在历史的暗夜中,它们未必就一定是相互仇视,可能是互不理睬,也可能是相互启发甚至是相互掩护。说到底,历史的真相不止一种,隐藏的手段亦多样,革命时期的情欲到底是禁忌和反抗策略,还是欢愉和享受,又如何分得清楚呢?叶弥如此对待情欲和历史,难免会让人联想到王小波。很显然,后者更乐于在两者之间设置一个怒目金刚的视角,采取一种更加直接的短兵相接的叙述策略。只是在一个不谈革命、懒得革命的泛娱乐时代里,王小波被人重新提起时,只剩下了空空荡荡的性,至于与性相关的历史则被毫无耐心地忽略了。叶弥的意图和实践或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她至少做到了一点:革命与情欲相遇的时刻里,他们的表情都是丰富的、意味深长的。这倒是印证了哈罗德·布鲁姆的一个观点:“我们读她,是为了人物,为了故事,为了形而上学的省思和情欲的省思,以及为了某种带反讽的处世哲学。”
叶弥并非突发奇想,刻意展示革命中的情色表演。在叶弥的观念里,革命年代里的故事不是只有悲情和血泪,革命本身也并非时刻都青面獠牙。那些有柔韧性的故事本身的光彩足以照亮暗夜里的某段路程,在这些时刻革命会显现其不易觉察的懈怠、脆弱、疲倦,革命虚弱的瞬间甚至会让人觉得竟有了温度和伦理。《美哉少年》便是这样的故事,不妨把它视为《风流图卷》的前传来读。
小说的第一章,作者描述了李梦安和妻子朱雪琴这“一对特别沉得住气的夫妻”的日常生活。“李梦安拿出他的《毛泽东选集》躺倒床上去看,他在书里夹了一本薄薄的《黄培英毛线编织法》,一九三八年出版,封面上套印着当时的电影明星周璇穿着毛线衣的照片,眼睛向下斜睨,作望穿秋水状。”“朱雪琴今天的目标是照着菜谱做一道药膳‘西瓜鸡’,她拿起她那本《毛泽东选集》进了厨房……原来她在选集里夹了一本手抄的菜谱。”“朱雪琴拿着勺子不经意地敲着李梦安的腿,勺子和腿共同制造出来的声音让她感到心里很安稳,那声音是结结实实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日常场景,包含了诸多庞杂而又极富意味的信息,它们可能为理论的介入提供了较好的例证,但是如何掌握阐释的限度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这些经验的魅力恰恰来自于各种意味微妙地融合、平衡、牵制而形成的张力,而非某种单调的倾向和形态。
《毛泽东选集》盖住了画册和菜谱,意味着革命对审美、日常秩序的否定和压制。坦率地说,这样的理解是政治非常正确的陈词滥调。事实上,把这样的细节仅仅理解为对故事发生语境的提醒,也未尝不可。反之,也可以把选择《毛泽东选集》作为封皮隐藏画册和菜谱理解为主动行为,这便意味着群众通过阳奉阴违的方式消解了革命的意义、抵制了革命的改造,从而最大程度的保全了日常。这似乎为巴迪欧所说的“群众沉默的威力”提供了绝佳的案例:“这是特殊惰性的威力”,是“吸收和抵消的威力,这种威力从此以后远远高于施行于群众之上的威力”。巴迪欧对“在沉默大多数”所造成的“阴影”效果有过经典描述:“退缩在私人生活中完全可以成为对政治事务的直接挑战,这是针对政治操纵的积极抵抗形式。角色颠倒过来:正是生活的平庸,正是日常的生活,即人们曾经谴责的小市民的东西,那些卑贱的非政治(包括性欲),他们成了重大时刻,而历史和政治事务则在别处展现他们那抽象性的意义。”不可否认,这样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并不认为叶弥描述这个场景,只是为了积心处虑制造一个精妙的隐喻效果。巴迪欧理论发生的原始语境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差别,是需要稍加注意的。百年来历次的革命动员中,基本的共同体意识几乎从未在群众中建立起来,比起群众的公共关怀和政治介入,恐怕更多的还是鲁迅所言的“做戏的虚无党”,在这里很难区分所谓的积极和消极的意义抵抗。而在革命的间隙或者革命出现倦态时,“敷衍革命”的背后恐怕还是朴素、顽强而又极具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的生存意识。
当妻子用勺子轻轻敲打丈夫的腿时,“食”与“色”的碰撞发出了“结结实实”、让内心“安稳”的声音,自然而又葆有意味和力量的精妙隐喻在这里诞生了,而此时“革命”真的在别处,淡淡的情欲开始升起,它同其他细节一样都在为隐喻的诞生做铺垫,然而暂时的满足背后却是关于未来的惶恐,因为“革命”其实并没走远,于是这个场景又多了一重意味。叶弥是洞悉这一切的,所以她才要尽可能而又极简地将其呈现出来,她最大的努力也是不让任何一种意味成为主导氛围的因素,而破坏了一幅信息凝练而意蕴驳杂的画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叶弥可能就是本雅明所怀念的那个“讲故事的人”:“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说到底,这其实是面对毛茸茸的历史图景和盘根错节的故事纹路,而采用的一种不引导、不归纳、不扭曲的“虚构”态度,借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说法,这态度非常“诚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