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站在比青藏高原更高的精神高地——《拉萨河的色彩》

用 生 命
诠 释 崇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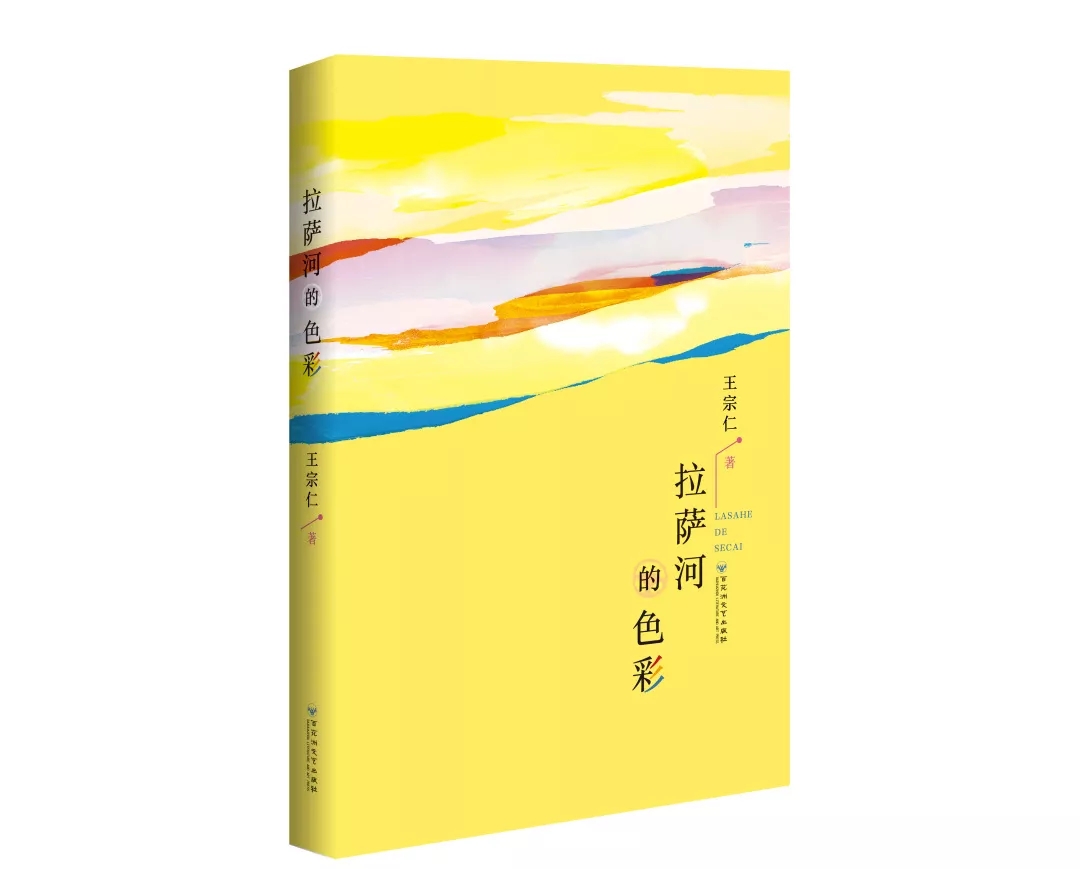
《拉萨河的色彩》
王宗仁/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定价:43.00元
编辑
推荐
《拉萨河的色彩》以平朴的叙述加上诗性语言的插入,意境高雅,富于感情底蕴。全书叙事结构独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故事性和画面感极强。作者的身份很特别,他是作家,又是当年奋战在青藏高原的英雄。在作品中,他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亲历者或目击者;既是写作者,也是被写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书写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
内容
简介
《拉萨河的色彩》一书把我们带到遥远圣洁的雪域高原,带到极具时间跨度(最早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唐古拉山,让我们结识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平凡中见伟大的人(最难忘那些超凡脱俗的年轻女性),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意义,领会到“崇高”的丰富内涵。
作 者 简 介
王宗仁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青藏高原当了七年汽车兵,出生入死,上百次穿越险象环生的唐古拉山到西藏。在逼仄的驾驶室里坚持写作。由于文学上的突出才华,奉调解放军总后勤部从事宣传工作。中国军旅文学的大家和中国散文界的宿将,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对于王宗仁来说,当汽车兵穿行于青藏线的七年刻骨铭心。身在京城,心系高原,像朝圣一样,多次回到唐古拉山,回到格尔木,或收集写作素材,或探访长眠的战友。在他的心目中,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是圣洁的“精神高地”。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出版文学书籍四十余种。青藏高原始终是他的创作母题。
自序:总会有一颗星在我头顶闪烁
常常有人给我提问:你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就那么心甘情愿吗?坦率地说,苦、累,甚至对生命的威胁都时刻存在。但我愿意面对。只因为我内心有一个难以抑制的支撑:一心要当作家。
14岁那年,上小学四年级的我写了一篇命题作文,我长大后的志愿是要到青藏高原去,当一名勘察队员,成为作家。为什么要把去青藏高原和当作家联系起来,当时我说不清楚,就是现在愿望变成了现实,我也道不出个所以然。反正自从在课本上知道了中国西部有这么个美丽富饶的青藏高原以后,就把它牢牢地放在心窝里了,常常做梦都到了那里。还是好奇多于理智。记得有一支歌曲《勘察队员之歌》,好让我喜欢,莫名其妙地觉得那些勘察队员都战斗在青藏高原,我常常哼唱着,有时走路也用脚和着节拍哼唱: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

我想象勘察队员在冰天雪地高原上的生活,勾画着我的作家梦。
也是14岁那年,我的处女作《陈书记回家》,在1955年第8期的《陕西文艺》发表。农村小娃娃在省级文艺刊物发表作品,确实罕见。我很得意,这篇作品的问世,缩短了我想去青藏高原当作家的距离。我的心更急切地飞向那个遥远的地方!
满天都是星星,总有一颗在我头顶闪烁。
生活中的巧遇常常不期而至。1957年冬,部队到我们县里接兵。当时我并不知道接兵接的是什么兵种,更不清楚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哪里,许是企盼走出农村的心情太急切,就辞掉了在一些人看来很不错的民办教师的工作,瞒着父母报名参了军。铺着稻草当床铺的铁皮闷罐火车,把我们这些还穿着老百姓衣服的新兵拉到兰州,又坐了四天的敞篷卡车,来到昆仑山下的汽车团。从此,我当上了一名高原汽车兵。我梦寐以求的上青藏高原的梦想,真的好像做梦一样,就这样似乎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作家梦呢?我却感到有些迷茫,但并没有断了念想。我相信和她毕竟有着可以用心灵交流的秘密。暂且将这颗早就孕育的文学种子埋在心底最肥沃的宝地,一场春雪飘来她会发芽!
直到我在汽车教导营学会了驾驶、修理汽车技术,第一次开着汽车从插在格尔木转盘路口,标志着“南上拉萨、北去敦煌、西往茫崖、东到西宁兰州”的路牌前起步,驶上2000公里青藏公路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实现作家梦想的路开始了。我强烈地感到可以从这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摄取足够的养分以滋养我的梦想。此刻,1959年初夏,一场“六月雪”正降临昆仑山。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雪,除了矗立的雪峰,就是被白雪几乎填满了的洼地。我特地刹住车,走出驾驶室朝通往四方的路上眺望,雪峰连绵起伏。近的那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把雪;远的那么远,可望而不可即。瞬间,我想象的翅膀随着这通往四方的远路展开,飞翔起来。我能走到我需要去的每个地方吗?未见得!生活中常常能遇到格尔木这样的转盘路口,你有时赶路的步伐越快反倒越容易迷惘和走失。不是吗?如果是逃路的人,保不准走着走着,脚印倒是种在了路上,前面却是一个又一个坟头……生活就是这样,找到一些谜团答案的同时,又引出了太多的悬念。你又不得不朝前方走去,再寻找。
我正这么想着,一阵来路不明的雪,被去向不明的风吹动,几个牧羊人赶着羊群不知该走向哪儿……
无意间,我发现路边的雪层上挺立着几丛荆棘,在这野性的荒原上,它默默地吮吸着积雪用过的阳光。正是它们守住了原始的蛮荒。
我采摘了几丛荆丛,这是诗心文眼。
飞雪和冰凌在方向盘上交汇,山路和戈壁在掌心重叠。敦煌、阳关、日月山、倒淌河、纳赤台、昆仑神泉、长江源头、拉萨河谷、布达拉宫……这些令多少人神往的鲜活得冒着仙气神韵的名字,是求之不得的文学原生态素材,从我踏着汽车油门的脚板下,一次又一次地闪过,刺激着我的神经,勾撞着我的魂魄。运输任务繁忙,经常白天黑夜连轴转地跑车,我只能利用开车中点点滴滴的空隙时间,见缝插针写稿。但是我真的写不好,只能乘着梦的翅膀回到驾驶室坐垫上,把所见所闻的事记在随身带的记事本上。创作需要走进生活,更需要靠近历史。于是我搜集我所在的汽车部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故事。我坚信,一个人如果有一把万能钥匙,就会有十万把能开的锁子。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文学原料,还愁变不成散文!
文学的路比我开初想象的远还要远。我寄出一篇又一篇散文,还有诗歌,天天等待开花结果。好不容易盼来自费订阅的报刊,战战兢兢地打开目录,寻找自己的那盏灯,可是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名字。我的灯却不知在哪个幽巷里蛰伏着。
往事不可假设,但未来是可以预测的。我踩油门的脚踏得更狠劲了,恨不得一脚就踏出属于自己的一本书!我把那些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还有从历史深处挖来的文学的夜明星、五彩路,继续详略得当地记在记事本上,积攒着,再积攒着,等待着爆发!
我一直不相信文学创作有一种永恒的理论,但我们还是需要它。在一些创作阶段,只有理论能廓清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从迷乱和人云亦云的混乱中轻松走出来。忽然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贵人,至今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其实说不说他的名字有什么重要,他只是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叫“师日新”。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他来高原深入生活,得知我痴迷文学,写了许多作品苦于发表不出来。他特地见了我,说了一番话,至今我记得大意是,文学创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想象艺术,最可贵的是创新。好像画家面对一张纸,下笔的地方有十个、百个,以至千个。到底能下笔的地方有几个,完全由画家自己。说实在话,他的话我当时似懂非懂。他还特地给我讲了诗人李瑛的几首诗。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师日新老师的指点,摸索前行。他是在启迪年轻的作者,要热爱生活,但还要走出生活,生活在文化里。这样才能做到既源于生活,又能高于生活。文艺创作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艺术,丰富是用来赞美简约的。
开车和写作是我成长中并蒂的两片绿叶,共享阳光,同浴风雨。我的那个记事本怎能不像口袋呢,里面装的是酿制文学的精米细面。我匆匆赶路,忙忙往里面填充,最后把自己也装进去了。

谁说通往春天的路上不是布满荆棘,汽车驶进昆仑山后,山体上不时有泉水飞流直下。昆仑神泉是不是相传的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路上洗理自己的梳妆台,另当别论。但是众人皆知这泉水最嫩的时候是大雪封山的季节。我的文学生涯在封闭和寂寞的意境里,经过相当艰难而幸福的跋涉,终于在这里亮起了一盏灯。
散文《昆仑泉》在1964年第6期《人民文学》发表。我接到这期刊物,无法掩藏的心花与刚刚落地军营外的春光接壤。不足2000字的一篇短文,速写了高原汽车兵和养路工人携手共守疆土的深情厚谊。一瓢水同样可以滋养根的生命。它给经过多少轮回才找到一盏灯的我,带来的冲击波是突破性的。整个春天,再加上整个冬天,我的心都是热的。怎能不热呢?就在不久前,也就一个月吧,我创作的反映高原汽车兵生活的散文《考试》,在全军举办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中获奖。这篇散文只有1500字,小散文折射的是大道理,它记述了汽车部队打破传统的考试模式,进行路考的新的考试方法。半年前,我把《考试》的手写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公用信纸上,寄到征文办公室,不久就在《解放军报》文化园地副刊发表。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它会获奖,惊慌大于喜悦。获奖证书寄到高原后,团政委王品一在全团干部大会上,把奖状高高举过头顶,自豪地说:“这是总政治部发的奖状呀!”至今,我依然十分珍惜地妥善保存着这个银色烫金、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红色大印的奖状。
差不多与《考试》获奖的同一个时间里,我的另外一篇散文的发表,不但惊动了汽车团,还让我家乡的亲人也着实受了一场虚惊。确切地说,那只是一篇小故事,题目《风雪中的火光》,发表在《解放军生活》上。内容真实地记述了我们的汽车被突降的暴风雪围困在唐古拉山上。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滴水成冰。为了保护汽车的水箱不冻坏,我们把棉军衣的棉絮甚至衣面都撕下来,蘸上柴油点燃烤车。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第二天早晨,暴风雪停了,我们重新上路。这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剩下线衣和单衣。我们把温暖给了汽车,为的是让它去温暖西藏人民。”那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解放军生活》节目,转播了这个故事。军营的战友们都听到了,我家乡的亲人也听到了。母亲得知我把棉衣生火烤了车,担心我会挨冻,赶做了一件棉背心,让父亲寄到部队。父母疼儿的爱心可以理解。我接到背心后,一直舍不得穿,只是在每次乘车路过唐古拉山时,特地穿上它,以留住那个发光发烫的岁月。
《昆仑泉》发表后,1966年第7期《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我的第二篇散文《夜夜红》,依然是反映高原汽车兵生活,但是无论从取材的角度及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对高原汽车兵在高寒地区执勤中的奉献精神,及面临的困境,物质匮乏和精神富有的反差,都有了比较敏锐的微察和细取。
需要说明的是,《昆仑泉》和《夜夜红》都是被两家报刊退稿后,我再次做了较大的修改,才得以在《人民文学》发表。我总相信,失败无处不在,成功就在你的身边。只等你去唤醒,冬去春来。
一个汽车兵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全军报刊上发表,引起人们的关注是不奇怪的。兰州军区文化部尉立青在1965年第1期《青海湖》发表了《可喜的收获——评王宗仁的三篇散文》,文中写道:“这三篇散文篇幅都很短,但很精。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极力地歌颂了高原的新风貌和高原人新的精神状态,使作品充满了炽热的时代激情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是三篇较好的散文。”这三篇散文除了《昆仑泉》之外,还有发表在《青海湖》上的《船》和《昆仑雪里红》。
说起尉立青,还有个有趣的小插曲。他来高原深入生活,同时为《连队文艺》组稿。他特地约我写一篇散文。我加班写了篇题为《裴大嫂》的特写,颂扬了某兵站一位裴姓男招待员热情、细心、周到地为过往兵站的指战员服务的故事,大家都亲热地称他“裴大嫂”。尉立青编稿时把文中的“他”都改成了“她”。编完后才恍然大悟,又把“她”全部恢复成“他”。他很风趣地对我说:“大嫂也可以是男人。我只好让‘她’回到男人的行列里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远方,渴望当作家的我对远方的渴盼似乎比一般人更强烈。远方不在起点而在尽头。尽头到来之前,它在哪里,好像很难一语道破。如果把你的远方比作灯火,这灯火挂得比星斗还高。你可以做到的是,双手要紧握阳光,不让它从指缝间滑落。1964年前后,我感到我离远方好像靠近了一步。只是靠近,远方并没来到。这个时间段,有三件喜事突然敲门,让我兴奋。一是我和我的同乡同学,同年入伍又同是汽车兵的战友窦孝鹏,携手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二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王积成来高原组稿,约我和窦孝鹏创作一部反映高原汽车兵生活的电影剧本。我俩一听就吓炸了,写电影剧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王积成告诉我俩,只要拿出初稿,他们会有人帮助完成任务。三是我把多年来发表的散文冠名《青藏线上》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希望能编入正在全国读者关注的“萌芽丛书”。分社收到书稿后编号登记,让我等待处理意见。
青藏高原四季落雪,雪落下来就会融化,融化后冬天就单薄了。不能不说,我的文学梦可以望得见“远方”在地平线上恍惚出现几缕曙光。虽然我明白,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奇迹终于会出现,让可能成为现实!
我又一次坚定信念,又一次抬起头踏上了茫茫青藏线!

最终,后面的两件事八字没见一撇就飞了!“文革”的战车碾过的地方,遍地都是光芒,但没有人知道这光芒有几多绿色,在这连森林也发呆的日子里,我偶尔也会望着几片枯叶想象我的“远方”。回忆失落的美好,反而让我长时间抱有希望和期待。我便尝试着恢复失落的、有点残缺的文学梦。因为生活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谁愿意看着原本多彩的日子变得死灰一样寂寞!
积累昨天的经历,创造今天的岁月,奔向明天的“远方”。
我继续创作,我真的巴不得将在风雪路上开车经历的故事,以及沉淀在脑海里的文学功底,都倾注到拉萨河里,用它的宽阔和流长孕育出一篇美丽的文章。没有发表作品的阵地——“文革”中所有的文学刊物以及报纸都停刊,或者改头换面,我的笔记本就是阵地。记的内容大都是我写“我”,又是在自己的阵地发表,在写作技巧上进行一点探索,甚至展现一些时代的盲区,野一点也无妨。一篇又一篇散文、诗歌,甚至报告文学,誊抄在我自备的大小不一的笔记本上,有的本子是很精美的印着“最高指示”的奖品册,有的是我买来的有副统帅举着语录本头像的纪念册,还有的是我自制的用画报包封皮的笔记本……我把它们统统称作“学步集”,一集、二集、三集……至今我仍然保存完好。我的许多散文就是从这个阵地上长出来的,我说“长”,是因为那些记下来的事情,仅仅是根,给它们添枝加叶后,就成了作品。那个隆冬,我在楚玛尔河畔写下一篇纪事后,看见河边孤独的冻土和叫不上名字的卑微的草根,独自承受一种凛冽,不知为什么我总想回头,走到文学的起点上去。也怪,就在我回过头的一瞬间,看见了“远方”的那盏灯还在闪烁。于是,我又把头收回,静静地贪婪地望着记事本里那些文学“胚胎”。
我在创作上的一个明显的拐点,或者说又一次爆发出火花,是1974年初春。当时我已经调到北京,在总后勤部宣传部任新闻干事,文学创作是业余爱好。平心而论,我调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主要还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帮了忙。1985年1月13日,我在《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我的两驾马车》,这两驾“马车”就是新闻和文学,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我的肩上拉着两套马车。我酷爱文学,也偏爱新闻。八小时之内写新闻,八小时之外搞创作。拉两套‘马车’当然要比单枪匹马费力了。但我心甘情愿……我总觉得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也许我的创作也会随之枯萎。”
话题再回到1974年初。一天,一封带着青藏高原早春暖雪的信飞到我手里,是刚从《青海湖》编辑部调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的杨友梅的来信。她在信上写道:“我很喜欢你写青藏线生活的散文,一直有个心愿,想把你这些作品汇集成一本册子,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实现。现在看来这项工作可以着手做准备了,请你把你的作品整理出来,寄给我看看……”
我惊喜得心都快蹦出胸膛了!我,一个曾经在风雪青藏线上开车的司机,几次送稿和她见面时都是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她接过稿件总会客气地让我坐在沙发上,询问我们汽车兵的一些情况。之后她就埋下头看我的稿,边看边用笔在上面勾勾画画。我总觉得我虽然坐在她身边,但离她那么远。哪里会想到她现在突然提出要给我出书,而且还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她在信中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集子里的作品必须有一半以上是新创作的,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我立即很兴奋地给她回信,详细谈了对要出版作品的设想,列了个提纲。从此,西宁—北京之间的信件频繁传递着创作信息。我每写出一批作品就捎给或邮寄友梅老师,请她指教。她从来不积压我的稿件,看完后总是及时和我联系。她对作品的标准要求很高,我新创作的或修改的作品,她总要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
其间,有一件事我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它多少也影响了我的写作情绪。她退回了我点灯熬油新创作的七篇散文,几乎全部否定。我把她长达5页的信反复看了好几遍,心中的不快和委屈才渐渐消散。信中她详细地谈了每篇散文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后来被教育部选入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语文第三册的散文《夜明星》,原文中有一段关于天葬的文字,她提出正文中有“天葬”二字就可以了,不必展开写,在文后加注释。天葬是藏族宗教信徒处理死者遗体的一种独特做法,三言两语在正文中很难说清楚,也没必要。她的意见是对的,我照办了。友梅老师还提出,将七篇散文中的两篇散文合二为一。她在信末写道:“我既然要给你出书,就会严格地要求你。”很快,我按照她信上的意见,对七篇散文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调整。寄她后,她又热情洋溢地回信,称赞修改后的作品不仅内容充实了,也有了较深刻的意境。她还高兴地告诉我,她编的工人作家程枫的小说集征订数为275000册。希望我这本书的印数也达到这个水平。
友梅老师在这期间常常利用她爱人老罗来京出差的机会,顺便给我捎来她改好的稿件让我誊抄,我则把修改好的稿件让老罗捎回。老罗每次都和我约好在我们部队驻地的万寿路地铁口见面,不见不散。老罗人很瘦,朴实,淳厚,话不多。我多次请他到机关坐坐,他总是笑笑,说很忙,以后有机会。可是,他始终没去。我每次见到老罗,总觉得他满脸忧郁,像有很重的心事。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老罗就是“胡风集团”的那个成员罗洛,我只知道他叫“罗泽浦”,我们都喊他“老罗”。十多年后,当“胡风集团”的冤案得到平反,罗洛也恢复了名誉,成了上海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一本又一本诗集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杨友梅也回到上海,在《收获》杂志社工作。回首往事,我真是又吃惊又不安。我仿佛做了一场梦。但是,一切都是真的。1975年11月《珍珠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
至今,我已经出版了45本作品集。
2008年4月,我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藏地兵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散文集是当时素不相识的年轻编辑丁晓平找上门主动向我组稿的。他在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这样的导读语:“比小说更精彩,比传说更感人。一个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军人,一个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写了四十多年高原军营生活,有数百名藏地的军人从他笔下走过。大家称他‘昆仑之子’。”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有一半以上是经过《解放军文艺》的编辑王瑛精心指点发表的。她告诉我:写青藏高原军营的题材,是你独有的文学资源,但是你不能只凭简单的经历和经验写作。当然,这样写也容易打动读者,却也容易失去个性,往往淹没在共性的洪流之中。她对我说,“你不仅要站在自然的海拔高度写高原军人的苦乐、死亡和爱情,还要站在人性的海拔高度去写。”她打了一个比喻:“如果你拿个碗在瀑布前接水,能接到水吗?”
我理解并践行王瑛的这番点拨,直到今天。优秀作品的产生不仅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对生活的思维模式,以及如何取舍生活,把原味生活酿制为文学作品。之后,我在探索摸索中创作了一批散文,不但取材有突破,写作也有了与过往不同。以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三篇作品为例:
《传说格尔木》,写了一位藏族老阿爸为了保护埋葬在戈壁滩女军人的遗体,赤手空拳与毁坟的野狼进行搏斗。他硬是用青筋暴起的拳头砸死了张牙舞爪的野狼。女军人是因为缺氧毙命的,老阿爸也是因缺氧献出了生命。女兵墓旁又立起一座新坟。《情断无人区》,展示了平息西藏叛乱中,发生在藏北无人区一桩离奇、悲凉,却引人深思的爱情故事。追歼叛匪头目的战士和匪首女儿,在无人区邂逅,碰撞出爱情火花,成婚、生子。后又各奔东西,女人进了尼姑庵,遗落在无人区的丈夫仍在等待、寻找藏女。《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反映了青藏线上第一个汉族女人给军营带来的满园春色,而她自己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后来,王瑛随我走了一趟青藏高原。她在和我的一次对话中说:“我上一次青藏高原,看见的青藏高原是一种样子,您年年上青藏线,写出的高原故事又是一种样子。生活和文学的这两种样子在记忆里重叠在一起,您对青藏线上官兵生活的感受,变为对生命在极限状态中所呈现的光辉的一种认知。而这正是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
也许,今生我再不可能上青藏高原了。但是,我还会写高原生活。因为文学,让我站在了比青藏高原更高的精神高原上!
2019年春节于望柳庄


